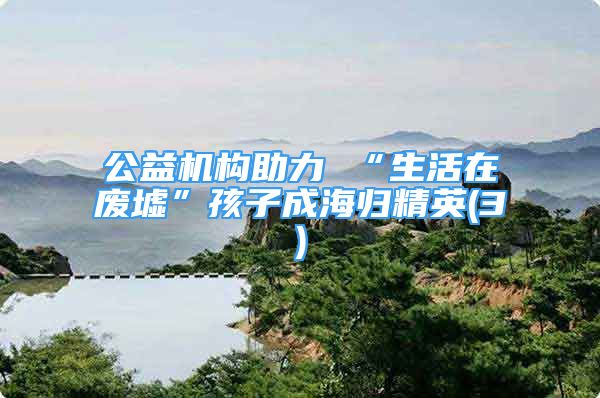


四
当年那群小伙伴里,不止屠文建一个人回到了久牵。
姚如惠是在11年前跟自己最好的朋友分开的。和当时不少久牵的小伙伴一样,她在初二时选择了一条最传统的道路:回老家,上高中,考大学。
那时她说自己想考回上海,然后做一个教育工作者,“因为教育可以改变人的命运”,“我想继承张轶超衣钵,在久牵工作”。
在老家,她一直努力学习,成绩也很优异。
直到最紧张的高三,张轶超告诉她可以申请国外的大学。经历一番纠结后,她休学一个月去北京参加了一个免费的托福培训。
后来,她也打印了UWC的申请书,只是当她把申请书递给她老家高中班主任时,班主任告诉她,这所学校就是个骗局。她爸爸也确信除了高考,这些都不是“正规”的路子。
她已经忘了怎么说服自己放弃出国的那个决心。她忽然相信如果一边准备UWC,一边准备高考,到最后会两手空空。
姚如惠最终没有寄出那张班主任已经签好字的申请书。那年4月,在还有两个多月就要高考的一天,她得知了王新月被UWC成功录取的消息。
拼尽全力,姚如惠最终考上了安徽大学。毕业后,她如愿来到久牵工作,负责一个分中心的运营。但她有新的计划:申请一所国外的大学,“到外面看一看”。
几乎每一个回老家读书的久牵孩子,在离开上海时都会像姚如惠一样眼神坚定说,自己一定会考上上海的大学,重新回来。但到最后,并不是每一个都能成功。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很难适应老家的教材、教学模式和学习节奏。他们很多都是独自回乡,只能选择寄宿。对他们来说,家乡更像是一个偏远、陌生的地方。
“一个教室有上百人,从早到晚都在学习,下课都没人出去。”一个曾经在老家读过初中的久牵学员瞪大眼睛,语气夸张,像是在描述一幕自己经历的奇观。
后来这个学生考上了老家的重点高中,但她拒绝入学。她相信3年的高中生活,“绝对会要了我的命”。
武子璇也是在初二时回家的。临走前,高中毕业的爸爸请她吃了她最爱吃的水煮肉片。可那天她没一点胃口,用筷子在菜里慢慢地拨来拨去。她不想回家,但爸爸告诉她:“你在这儿,只能上个中专,发展空间就小了。现在回去了,以后可以再回来。”
她从小就表现出了那种对音乐“无法自持”的热爱。屠文建记得他们第一次参加合唱团时,台上放了一架钢琴,站在人群中的武子璇不由自主地把手伸了过去,然后招来老师的一阵教训。
在上海时,她有空就跑到久牵,坐在那架志愿者捐赠的钢琴前,弹上一天。有一次他们合唱时,伴奏的老师没有去,武子璇就坐在钢琴前临时伴奏,惊艳了全场。
回老家后,她再也没机会弹钢琴。课表上的音乐课被改成自习,音乐教室里有架钢琴,却常年锁着门。后来,她只能等没人时,偷偷翻窗户进到音乐教室里,一个人在里面弹上一段。
她也喜欢小提琴,因为她的热情,上海的志愿者为她线上教学。这几乎成了她老家那个小县城里的奇事:连续一年多,每天早上都有个小姑娘在网吧,站在电脑前,对着屏幕,旁若无人地拉小提琴。
2014年暑假,武子璇回到上海,久牵的好朋友激动地抱住她,告诉她自己结婚的消息,让她一定来参加。武子璇显得有些局促,支支吾吾地告诉对方,自己在老家,参加不了。朋友尴尬地放开了她,“感觉她一下变成了一个外来人。”
武子璇说:“爸妈让我回家了,不想跟他们有太多交流。”
随后,武子璇自己坐到钢琴旁,掀开琴盖,完成了一曲独奏。她没有表情,手指逐渐加快速度,曲子的高潮部分激昂澎湃。
她曾说:“音乐可以把我不想说的话表现出来。”那时,屋子里的小伙伴打闹在一起,声音嘈杂。
去年,武子璇在老家参加了高考,成绩没有达到二本线。今年她复习后,再次高考,如今正等待着这个能让她命运再次改变的岔路口。
10年后,那些曾经发誓要回到上海的孩子,大多已经杳无音讯。有几个还与久牵保持着断断续续的联系,他们中间有人留在了老家,做了小生意,看上去很满足;有人高中毕业后跑去南方打工,和老家的孩子已经没什么两样。
屠文建也承认,自己和那些回家的久牵学员已经是“两类人”。
去年,他小时候在久牵的“大哥”忽然打电话,向他借钱。他没想太多,就借给了他。后来,自己爸爸出了车祸,屠文建让这个现在在贵州老家的“大哥”还那几百元时,电话那头却传来“我不认识你”的声音。
复旦大学副教授熊易寒,把久牵的这群孩子称为“城市化的孩子”。他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写道:“他们都是在当代中国高歌猛进的城市化浪潮中出生和成长的,自身也经历一个城市化的过程。乡土性从他们心性中剥离,与此同时,城市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塑造他们的心智、观念、气质和认同。最后他们经历的痛苦、彷徨、迷失是由经济上吸纳、政治上排斥的‘半城市化’带来的。”
他深知“命运”这个词与社会科学强调的精确性和价值中立格格不入,但这个农村出身的政治学副教授相信:不关注命运,政治学就缺少震撼人心的力量。国家、市场和社会是“命运”的主要塑造者。
五
那些当初选择留在上海读中专的久牵学员,现在也都已经工作了几年,走进了社会。
2010年时,刘燕霞、姚如惠和王新月3个人曾一起去北京参加过托福培训。最后,王新月成功出国留学,姚如惠在老家考上了大学。刘燕霞在申请UWC失败后,留在了上海读中专,走上了一条和她们俩完全不同的路。
中专毕业后,她在拜耳集团找到了一份实验室质检员的实习。那是她第一次进入那么大的公司,也非常认同集团追求自由的企业文化。
“他们不像别的公司很小,限制你很多事情。”在一次采访中,刘燕霞面带微笑,眼神里充满憧憬说。她希望自己能留下来,“10年后,我希望自己不再是个一线的质检员,而是能够涉及销售的工作。”
这次实习通过了层层面试,父母对她留用的期望也很大。母亲告诉她,实习时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也是值得的,“每月4000元的工资很不错”。
“爸爸妈妈给你带出来不容易,给你养大了,成人了,下面的路就由你自己走了。”在狭小的宿舍里,一张简易的饭桌前,母亲对刘燕霞说。
被通知无法留用的那天是个阴天,在租来的房子里,她放下电话后,跪在床上靠近墙角的地方,哭出了声。
“其实我也知道文凭很重要,有时候一想到自己的未来真的会哭。”她闭上眼抽泣,“我应该留在重庆读初三,然后考高中,考大学,我当时是不是选错了?”
后来她去外滩散心,她说每次看到黄埔江,就会想到小时候的自己。十几年前,她的父母卖掉一年的收获,买了两张船票,坐了7天7夜的船从重庆来到上海。
“这个城市很美啊,可这里很多地方无形中告诉我,我不属于这里。”江风呼啸,她靠在岸边的栏杆上,望着陆家嘴那些灯光璀璨的高楼说。
她不知道以后在上海,自己的小孩怎么办,“不想因为我的能力而耽误了他”。她的父母也常常抱歉地对她说,“因为我们的关系,不能让你更好的条件,但是你自己不要放弃”。她说每次听到这些话,自己都会哽咽。
在上海,因为频繁搬家,即使回到爸妈旁边也没让她找到家的感觉。
事实上,在上海市官方文件的认定中,她家的房子只能称作“临时住所”,这也成为他们在上海享受不同政策的一项认定标准。
2013年特大城市人口调控政策出台后,上海市随即发布了《关于来沪人员随迁子女就读本市各级各类学校实施意见的通知》。《通知》里“合法稳定就业”和“合法稳定居住”的两项规定,把大部分农民工子女挡在了中小学门外。
因为这两个新的限制,屠文建10岁的弟弟不能在上海读初中了。
“合法稳定就业”要求他们提供连续的社保缴纳证明,这对经常打“临时工”的父母来说很难做到。而“合法稳定居住”则更难实现,按照规定,即使是租房,也需要提供房东的房产证,他们承担不了这种房子的租金。
事实上,这十几年,城市不断扩张,他们曾经的聚集区,早就建成了新江湾城,价格已经涨到8万元每平方米。
他们的家从国权北路的一头,一直搬到靠近城市边缘的另一头。再到后来,他们分散开来,分散在这一区域的角角落落,时刻准备着寻找下一个住处。
“公办初中进不了,民办的上不起,周围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也早就取缔完了。”屠文建苦笑着说。
弟弟出生在上海,在久牵长大,从来没有回过老家。明年他就要和父母一起回老家上学,他会经常问哥哥,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能在上海了?为什么?
屠文建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没法给弟弟解释他根本理解不了的户口。只能笑着对他说:“是啊,回家后要好好学习。”
中专毕业后,没有被拜耳集团留用的刘燕霞经人介绍找了一份在面包店包装蛋糕的工作,但她很快把这件“没有创造力”的工作辞掉了。再到后来,她结了婚,很少再在久牵出现过。
这些还在上海的久牵学员,有人依旧保持乐观,拥有一颗“大心脏”。有人变得现实起来,开始抱怨社会的不公,用钱和地位丈量一切。
这个夏天,他们又聚在一起,就像小时候一样。
“几个留学的在一起,聊的都是国外的事情,他们很有话题,但我们就插不上嘴。”有人觉察到了这种异样。
姚如惠也感觉到了这种变化,她说这是久牵最不愿看到的,但它又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现在几乎所有久牵学员的家长都知道了UWC,不管孩子同不同意、适不适合,都让他们报名申请,然后全力准备面试。久牵一直希望孩子们身上能带一些理想主义,这件事却让久牵看起来像一个考试培训机构。
这些久牵前辈们偶然间找到的路,现在竟变成了独木桥。
在上海生活了10多年的屠文建,仍然觉得“肯德基就是这个城市的味道”。他还记得自己小时候第一次吃肯德基时的感觉,是爸爸带给他的。那个味道让他记忆深刻,以至于到现在他还对肯德基念念不忘。直到多年之后,他才得知,当年那个肯德基汉堡包,是爸爸在外面捡来的。
责任编辑:尹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