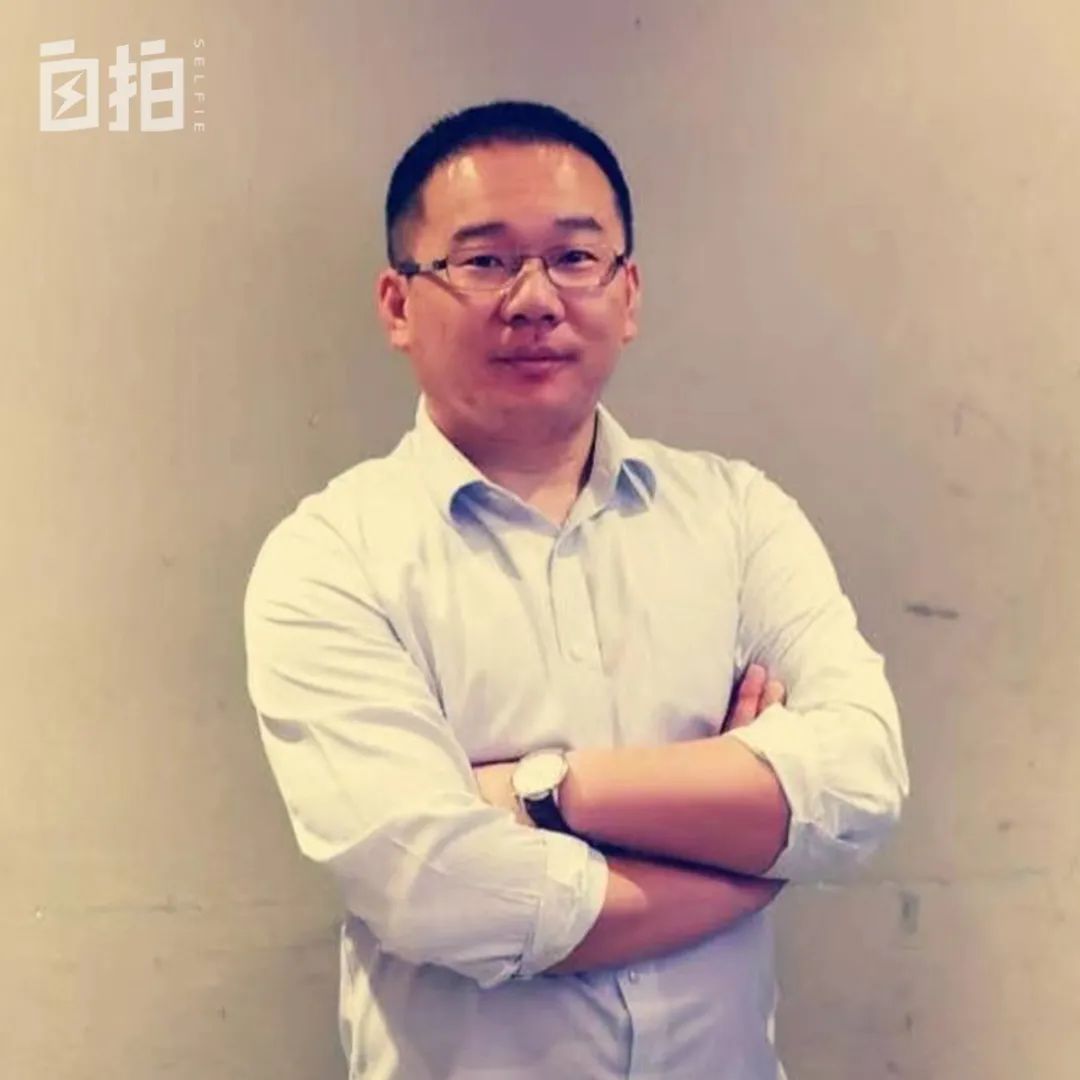刘栋/口述
Rain/撰文
我叫刘栋,1986年出生于河南濮阳农村。为了不过苦日子,我从小立志出人头地,17岁便考入著名的985高校“西北工业大学”。
2008年大学毕业,我踌躇满志地进入社会,不巧赶上金融危机,怎么也找不到心仪的工作。
为了解决温饱,我只能先去饭店打工,没想到从此留在了餐饮行业。过去这十二年,我从杀鱼工、传菜员一路做到副店长、店长,如今是一名年薪50万的资深餐饮经理,已经在上海买了房和车,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
我的近照,在餐饮业吃得好,身体有些发福了。
其实房车都是其次,我最在乎的是家的感觉,因为从小到大,我对家庭的记忆一直都不太美好。
我的父母都是农民,原本感情和睦,他们一直靠种地下苦力为生,父亲偶尔还会织网打渔、做点木工活儿。生活虽然清苦,日子总归过得去,然而,这段美好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
随着我们三兄弟慢慢长大,吃饭、上学的开支越来越多,种地的收入已经不够支撑,家里一天比一天紧巴。母亲整日发愁,父亲却破罐子破摔,变得越来越懒散。
他时常窝在村头的小卖部,和一帮闲人称兄道弟,通过打牌、喝酒寻得一时放松。这在受过高中教育的母亲眼里,是典型的不务正业。
父母和我们一家三兄弟,我排老二。
从那时起,父母开始频繁吵架,有时候是为了一日三餐,有时候是因为家庭开支,还有几次和我们三兄弟将来娶媳妇有关。
母亲担心家里太穷盖不了房,怕三个儿子只能打光棍,总是提醒我父亲多想办法挣钱,但父亲不仅不听,反而变本加厉,和牌友们聚得更勤了。
母亲心凉了半截,怨气也越积越多,直到矛盾彻底激化。有次弟弟发高烧,母亲带他去了村头小诊所看病,大夫却马虎地用错了药。母亲知道后气不过,一直想问对方讨个说法,父亲却碍于面子不肯去,只想息事宁人。
在激烈争吵直至动手打架后,母亲带着三个孩子中最乖的我离家出走,回了陕西西安的娘家。
我在西安姥爷家的照片,不用听父母吵架拌嘴很开心。
这一去就是两年,后来父亲和爷爷找来好言相劝,总算把我和母亲接回了河南。或许是感情余温不在,亦或是想逃离一眼望到头的农村生活,回到父亲身边一年后,母亲便孤身一人前往西安打工。
自此,我、大哥和弟弟过起了类似单亲,其实更像是孤儿般的生活。母亲不在身边,父亲又很少管我们,以至于我们三兄弟总觉得在村里低人一等。
每年春节看着其他小孩穿着新衣服新鞋,在马路上放肆地玩鞭炮,我们都打心眼儿里羡慕,怕穿着旧衣服被人瞧不起,很少会走出自家的土屋。
种种委屈,被年少的我埋在了心底,我在学校一直刻苦读书,立志要比村里那些爱说闲话的人强。
每每回到村里跟父亲下地干活,汗流浃背地种麦子、割麦子、种花生、掰玉米,我总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要离开这无尽的麻木和贫苦。
我家的地,以前靠人种庄稼,如今靠机器。
中考结束,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高中后,父亲却连每学期三四百的学杂费都拿不出来。那时的我有一种预感:接过父亲手中的锄头继续当农民,似乎要成为我逃脱不了的宿命。
幸运的是,母亲了解到情况后,决定把我接到西安继续读书。经过三年的寒窗苦读,我最终以580分的高分考上了理想中的名校——西北工业大学,进入经济贸易专业就读。
大一入学报到后,我在学校公示栏看到一则通知,说大学生入伍两年再返校入学可保留学籍,学费还能全免。这个政策对我而言简直是及时雨,既能报效国家,又能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我立马决定参军入伍。
刚进部队时的我,个头矮小,稚气未退。
当我来到河南新乡的部队时,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秩序井然、威严肃穆。当时我个头低,套上宽大的军装更显瘦小,对即将到来的集体生活既期待又忌惮。
很快,我就面临入伍训练的第一课——叠被子。刚开始怎么也叠不齐被角,为了模仿成连长叠成的豆腐块,我不得不把水洒在被子褶皱的边角,来回揉搓,才能叠出笔直的棱角。
将近一周时间,我都是裹着浸湿的被子入睡的。
新兵训练结束后,我成为一名通讯兵,既要接受严苛的体能训练,比如爬冰卧雪、匍匐前行、扛八一杠跑五公里,还要掌握莫尔斯电码通讯诀窍,做好信息传输工作,身体和脑力都要经受极大的考验。
我在单杠上做体能训练,身体慢慢变得硬朗。
当时带我的班长就和《士兵突击》里的史今班长一样鞭策我们:不要轻言放弃,坚持下去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但不坚持一定没结果。我带的兵都要全力以赴,从一而终。
因此,我每次跑五公里时都死命地往前冲,不断突破身体的极限。轮到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我就比别人多付出一倍的时间,站岗也不忘背诵复杂的通讯代码,后来在集团军技能专业比武中,我不出意外地取得了第一名。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我这个大学生也成了即将离开的老兵。退伍那天,连长将沉甸甸的肩章、军衔从我身上取下,换上了一朵大红花,对我交代:以后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听到班长的这句话,我顿时热泪盈眶。
2004年,我从部队回归大学,十分珍惜落下的读书时间,每天一下课就飞毛腿般跑去图书馆占座,巩固专业课知识。
那段时间还静下心读完了《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这本书影响了我的价值观,让我知道无论生活再苦再难,都应该像保尔·柯察金那样去面对。
大二时我在公园游玩,看起来仍有书生气,但已经比以前成熟了很多。
我每天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勤工俭学。那时在麦当劳兼职一小时才挣三块六,要刷厕所、洗盘子、送餐,什么都干。我每天抽出三个小时去做兼职,周末也不歇,一个月挣300块钱便能满足我的伙食费。
到了暑假,我就去舅舅家的水站帮忙。夏天生意很好,我每天要骑着摩托车将桶装水送到很远的地方,一天大概70桶。有几次遇上电梯出故障,我只能一步一步爬楼梯,最高爬过16楼。
身体里的盐分通过汗水不断析出,T恤上常常留下一大团白色汗渍。脱下衣服,可以看见黑白分明的两种肤色。
送水期间,我在网上里认识了一个学妹,家境很好。她听说了我的经历后没有嘲笑我,反而很欣赏我身上的韧劲,和我聊得火热。
我把这事分享给了别人,却被质问:你有没有告诉那个女孩儿,你现在是在送水?你有没有告诉她你是从河南农村来的?
这话听起来很刺耳,自尊心驱使我赶紧结束这种生活,去远一点的地方工作。
2008年毕业之际,恰逢金融危机暴发,我本来已经在校招中被山东一家上市公司招录,结果刚做了3个月实习生,基本业务都还没熟悉,就被列入裁员名单,面临“毕业即失业”的窘境......
我的大学毕业证书复印件,当时没怎么派上用场。
难受归难受,我还是得抓紧时间找工作,考虑到北京工作机会多,我决定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北漂。
他们俩属于家里条件比较好的,人手一台小灵通手机,而我来北京时只揣着实习时挣的3000元,电话号码都在一个小本子上记着,打电话只能揣着本子去电话亭刷电话卡。
初到北京,看到有剧组在招群众演员,而且还开出了诱惑性的工资——月薪1500元,我就和两个同学一起去应聘了。
每天早上三点,我们就得从大通铺上爬起来,赶着大巴车前往河北,到太行山上去拍《八路军》。大老远跑过去,偶尔在一些场景排个队露露脸,当个工具人,一整天时间就晃过去了。
拍戏时总是尘土乱冒,后来我也没能在电视剧中找到自己。
做了半个月后,我便放弃了这份华而不实的工作,继续寻找专业对口的岗位。因为是提前离开,我连之前的报酬都没拿到手,一起北漂的两个同学则继续留在剧组,梦想着一夜成名。
彼时已到冬天,走在北京的街头,我觉得格外冷,咬咬牙花400块钱买了一件羽绒服,决定先给自己找到一个容身之所。
在马路旁的柱子上,我看到了地下室月租300元的广告,对比了其他地方,还是觉得地下室性价比最高,于是提着行李住了进去。
当时住的地下室和这张照片上的差不多,如今已经很难租到。
我睡着一米左右宽的小床,床沿和门之间只有一双鞋的距离,在这个和厕所一样逼仄的房间里,我总算体会到了人们常说的“蜗居”是什么感觉。不大的地下室一溜开辟了七八十个小隔间,租户们来自五湖四海,嘴里说着各种方言。
蛰居在这样的地方,我的内心反倒安定下来,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畅快。
白天,我穿着那唯一的一件羽绒服,在各大人才市场找体面的工作。晚上就回到散发着霉味的负三层地下室,或是拿着身份证去负二层的网吧继续投简历。整整两个月,我都是在投简历、面试、面试失败的反复折腾中度过的。
当时住的房间还没有我家现在10平米的厕所大。
每次在地铁上看到穿着光鲜的陌生人,我都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他们那样,摆脱湿气很重的地下室,跻身成功人士的行列。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很快,我兜里3000元的闯江湖资本只剩下20元,地下室的租期也只剩一个星期,我连三块钱一屉的包子都负担不起了。
为了解决温饱和住宿,我决定先在餐饮行业做一下过渡,于是来到大学旁边的一家韩国烤肉店,干起了900元月薪的传菜员。我每天早上9点开工,晚上10点下班,负责从负一层的厨房传菜到地上。
虽然都在室内走动,但工作强度很大,两周时间便跑坏了我那双从批发市场买来的皮鞋。
我在后厨帮忙,身上穿着廉价西装,戴着围裙。
我心里很清楚,这份工作只能当作过渡,干满4个月后攒下点钱后便主动辞职,再次回到晚上住地下室、投简历,白天跑人才市场的生活。
虽然不断完善简历,但始终石沉大海,我攒下的那点生活费很快就见底了。最窘迫的时候,我只能和朋友分吃一张白面饼。
接连的失败让我明白:温饱比体面更重要,于是,我彻底放下了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光环。当一家餐饮公司给我打电话通知面试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这家公司有很多连锁店,他们希望招我为管培生,起始工资开到每月2000元,还包吃住,我一下子被吸引住了。管培生的名头听上去很高大上,但我知道,进去肯定还是要从最基层的岗位干起。
当管培生时在餐厅门口的留影。
我已经做好了要轮岗的准备,结果被分到的第一个岗位竟然是杀鱼工。店里火锅生意好,每天都有大量的活鱼需要宰杀,我要把鱼从池子里捞起来砸晕,刮干净鱼鳞后开肠破除。
一天下来,巨大的鱼腥味像是长在了身上,洗都洗不掉,我心里泛起强烈的落差感,觉得自己被大材小用了。
坚持到第三天,杀完鱼去洗碗间拿餐具时,一位顾客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太好吃了,特别棒,师傅辛苦了!”虽然累得精疲力尽,但这句鼓励让我体会到了辛苦劳动的价值。
在轮完杀鱼工的岗位后,我又先后轮了9个岗位,最后考核打分时,我在7个岗位上的轮训得分都是100分。
也许是我踏实好学的态度打动了店长,她决定给我一个带队管理餐厅的机会。适逢公司要在西单华威商场开一家分店,管理人员都是新人,店长便力荐我去竞聘。经过三个月的严格考核,我成功由管培生升至副店长,工资也从2000元涨到了4800元。
升职后的某天,我夜里一点还在加班做预算,那时电脑还是Windowsxp系统。
后来的一年多时间,我通过带团队、拓展专业知识,又从副店长升到了月薪6000元的店长。权力和责任是统一的,为了完成门店的业务指标,我经常从早上10点一直干到晚上12点,加班成了常态。
但回报也是丰厚的。当上店长后第一年,我就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年终绩效拿了10万。
对内,我努力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对外,我不断拓展业务渠道,经过两年半的磨练,我在2013年又升到了公司的资深经理,被派到内蒙古全权负责三家连锁店的日常经营。
在公司干满三年后,我获得年资奖奖励。
这个伴我从基层成长起来的公司教会我一个道理:一个餐厅的发展是靠一个团队支撑起来的。正因我从一线做起,所以我很尊重团队里每一位员工,无论是管理者还是洗碗工、保洁阿姨。
有次一位传菜工的爸爸突然出车祸,他想临时请假回家。得知消息后,我马上帮他买好车票,将慌乱收拾好行李的他送到火车站,临走时拍拍他肩膀:“别担心,等你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完再谈工作。”正是这份体贴,让店里的所有员工都很敬重我。
我和店里同事的合影,拍照时大家总是让我站中间。
2015年,当我告诉大家我要离职去上海打拼的时候,团队所有员工都哭了,他们舍不得我走,但我不得不得开启新的生活,因为这一年,我和相识两年的江苏姑娘结婚了。
她在上海做外贸工作,曾在我短期到上海分店出差时有过一面之缘,后来加了微信,彼此很聊得来。考虑到今后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我不能这样不负责任,一直和她分隔两地。
我和媳妇的合影。
2016年1月,我将工作以来攒下的所有财富拿出来,在上海嘉定区贷款买了套将近80平米的房子,首付47万,房贷要还107万,虽然听起来让人很有压力,但我和老婆总算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
同年10月,为了迎接孩子的出生,我又按揭买了辆车,付完款全身上下只剩下3000元,好像一下子回到了人生起点。
我家的房子,虽然不大,但装修得很温馨。
2017年,我被某知名连锁餐厅聘为为门店经理,但因为要管理的门店离家太远,没办法陪伴老婆平安生产,索性辞职陪在老婆身边。
2018年,我重回职场,为了了解餐饮实体企业和互联网的未来发展趋势,我到上海的一家机器人餐厅做了店长,公司给我开了年薪50万的工资。
我有幸接触到了互联网的浪潮,但后来领导又委任我去做零售项目,我思前想后婉拒了,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扎根餐饮行业,总觉得学习把菜做到极致,才是这个行业最值得尊重的。
于是我又回到了传统餐饮业,成为一家连锁火锅品牌的餐饮总监。如今在管理岗位的我压力很大,也闲不下来,时常想着在后疫情时代,我所管理的火锅店是不是很难在全国各地开花,能否用用极致的服务打动顾客。
因为工作日太忙,有时还会出差,宝贵的周末时间,我都会用来在家陪女儿。
我出差回来后经常陪女儿玩,这是最放松的时刻。
每天晚上九点半下班,我从餐厅回家需要坐2个小时地铁,我习惯于在这条回家的路上不回信息、不打电话,看着地铁经过高楼林立的闹市,也穿过冷清寂静的城中村,静心感受这座城市的余温。
漫长的等待之后,我终于回到令人心安的小家。每当打开家门的那一刻,我都觉得过去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
从一无所有到有房有车,拥有自己深耕的事业,我的人生已经足够幸运。唯一能做的,就是继续折腾下去。